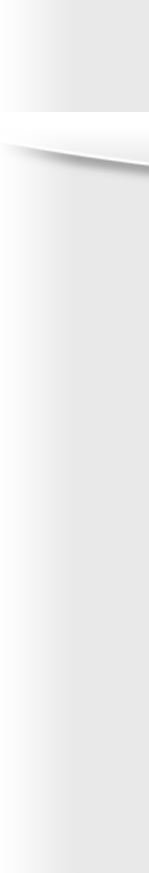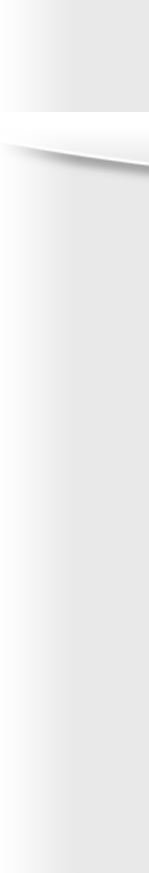01 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性质
理论层面,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范围广于关联交易。基于侵权法逻辑,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确立关联交易损害赔偿制度。《公司法解释(五)》第1条细化裁判规则,重申公司诉权,激活股东代表诉讼,实现两大制度的紧密衔接。
司法实践中,主流是将关联交易行为人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纳入侵权范畴审查。如本期刊登的“关联交易行为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一文,二审判决遵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尊重商业习惯、弘扬契约精神,同时肯定关联交易积极面。
责任主体方面,《公司法解释(五)》限定列举了双控人与董监高这5大责任主体 。对于5大主体之外的利害关系人,像配偶、子女等近亲属是否涵盖其中,并未明确。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将董监高的近亲属、其他关联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纳入,但对双控人的近亲属、其他关联人未作拓展明示。
司法实践已开始精准锁定责任主体,严格区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由。
《公司法解释(五)》一大亮点是明确排除被告人免责抗辩事由。只要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就能依据民法典第八十四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要求双控人、董监高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不能仅以交易已履行信息披露要求、经股东会同意等法定或章定程序作为抗辩。因为关联交易需同时满足“信息透明、对价公允、程序严谨”三项基本要求,任何一项缺失或存在瑕疵,都构成重大法律瑕疵。即便满足“信息透明、程序严谨”,若不满足“对价公允”,仍侵害公司利益,程序和信息披露不能必然保证交易公允,所以无法成为被告免责事由。
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组织性,存在系统性道德风险,且受害公司、无辜股东与关联交易行为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为减轻公司举证负担、提高侵权失信成本、降低失信收益,关联交易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应遵循严格责任(客观责任)原则,而非过错责任原则。既然是客观归责的侵权责任,就不要求原告举证被告对关联交易存在主观恶意或重大过失。若裁判者坚持过错责任说,也应采用过错推定规则,由被告自证清白。
公司对不当关联交易侵权责任之诉的诉请不局限于赔偿损失。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列举了11种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这些方式可单独或合并适用。所以,受害公司除主张损害赔偿,还能主张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权利。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董监高履职违法或违反公司章程时对受害公司的赔偿责任,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对不当关联交易的归入权。董监高从事不当关联交易违反忠实义务,公司可依此行使归入权。归入权本质是消除董监高不当利益,法理依据源于信托法中的推定信托制度,在公司法与证券法中均有体现,目的是遏制道德风险。我国2019年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董监高与持股5%以上股东短线交易时的公司归入权制度。
司法实践中,法官已关注到索赔权与归入权的协同关系。如“公司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适用”一文,法院认为判决宋某飞返还470万元时,公司可行使归入权和索赔权,最大程度保护公司利益。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归入权与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短线交易归入权类似,但适用领域不同,前者在公司内部治理,后者在二级资本市场。
公司归入权优势明显:一是兼具惩罚性与补偿性,不以公司损害发生为前提,本质上惩罚性未脱离补偿性;二是原告公司举证负担轻,只需对董监高失信行为及不当收益初步举证;三是法院裁判难度可控,查明董监高不当收益后可直接判令归公司,无需增减金额。
但归入权效力有局限,范围限于董监高不当所得,无法涵盖公司超过该所得的损失部分,所以不能替代公司依据合同法或侵权法的索赔权。
董监高失信所得与公司损害关系复杂,在不同情形下,归入权和索赔权发挥不同功能。索赔权行权成本低,归入权应是公司首要救济途径。公司起诉时若无法确定董监高不当所得与公司实际损害大小,可同时列举两项诉请,法院应受理,且不应苛求公司另行诉讼。公司惩罚性索赔权与归入权可有机融合,公司基于理性自治和契约自由,可对恶意失信董监高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两者可一并主张。
作者简介

石倩倩律师,女,中共党员,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现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专业领域: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劳动纠纷、公司法务等民商事领域的诉讼业务、执行业务及法律顾问等非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