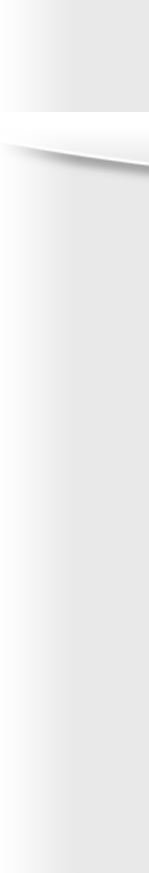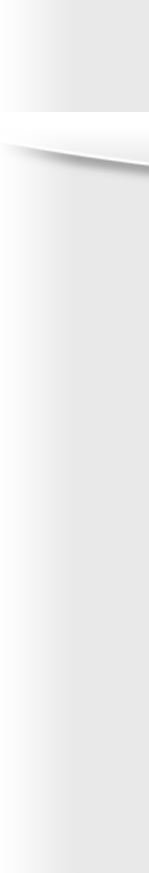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某和李某事先预谋“找个女的抢钱”,郑某事先已打算抢劫过程中要进行强奸,但李某事先并不知郑某还要进行强奸。2011年8月6日深夜,二被告人开车把被害人陈某(女)骗上车,后带至江边。二被告人共同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行把被害人陈某拖至江边一偏僻树林内,被告人郑某把陈某推倒在地,并让被告人李某去拿刀以此恐吓陈某,郑某威胁陈某把衣服脱光,被告人李某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也没去拿刀。后被告人郑某对被害人陈某进行了强奸,并让被告人李某去翻陈某包内财物。李某看到郑某在强奸陈某而未做声,在相距约一米的旁边将陈某包内钱物取走。所劫取财物,二被告人平分。[1]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的定性,对郑某和李某均构成抢劫罪,且系共同犯罪,以及郑某另外构成强奸罪没有异议。问题在于李某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共犯。李某在郑某强奸过程中并无积极的作为,能否成立不作为共犯?对此,存在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郑某实施奸淫行为时,李某只是在一旁翻陈某的包,李某既没有奸淫的故意,更也没有强奸行为。因此,李某不构成强奸罪的共犯。
第二种意见:虽然李某没有实施奸淫行为,但是李某先前与郑某共同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作为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李某具有阻止郑某强奸罪的义务却没有阻止,对郑某实施的侵害陈某的性的自决权具有物理的因果性,李某在郑某的强奸过程中起到帮助作用,应成立强奸罪的不作为帮助犯。[2]
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同样认为李某先前与郑某共同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作为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李某具有阻止郑某强奸罪的义务却没有阻止,成立不作为犯罪。但是,李某是不作为强奸罪的实行犯,而不是第二种意见所主张的帮助犯,他与郑某的作为成立共犯,只不过他在这里所起的是次要作用,可以认定为强奸罪的从犯。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李某因先前行为负有阻止郑某强奸犯罪的作为义务
刑法理论认为,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使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处于危险状态的,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这种危险或者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导致产生危害结果的,构成不作为犯罪。不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首先要有作为义务。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包括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先前的行为以及基于合同等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3]
本案中,李某先前与郑某对陈某共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既是二人共同抢劫犯罪的暴力、胁迫方法,也是郑某强奸罪的暴力、胁迫手段。李某的先前行为是他和郑某为了抢劫犯罪共同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即李某的先前行为属于抢劫罪构成要件中暴力、胁迫部分的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先前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不能一概而论。为了防止重复评价,有必要把刑法上就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和因发生严重结果成立另一重罪的情形排除在外。本案中,李某的先前行为是抢劫罪行为,之后郑某实施强奸罪的行为,刑法并没有在抢劫罪中就发生强奸罪的结果规定为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或者另外规定为一个重罪。因此,李某实施抢劫犯罪的暴力、胁迫行为属于先前行为。但是,这一先前行为如果要引起强奸罪中的作为义务还要符合下述要求。
作为义务的来源虽然包括先前行为,但是,先前行为还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才负有作为义务,即先前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实施的,对法益造成了现实、具体、紧迫的危险。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的先前行为都可以作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刑法上必须对其加以实质上法义务根据的限制。否则,就会过分扩大处罚范围。这种限制就是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的危险时,行为人才具有保证人义务。[4]具体到本案中,李某的先前暴力、胁迫行为使陈某的人身陷入现实、具体、紧迫的危险状态,使得陈某的性的自决权这样的法益处于危险之中,李某这时具有了避免陈某性的自决权被侵害的义务。因此,李某负有阻止郑某强奸犯罪的作为义务。
(二)李某成立强奸罪的不作为正犯
客观方面,不作为是特殊的行为。不作为是指对他人的犯罪行为不予阻止放任不管的行为。不作为也要作因果关系的考察。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自然的、存在的,需要作刑法上的规范判断。对不作为来说,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性而言,主要是物理性的因果关系。不作为共犯是通过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以作为的正犯为中介,仅对结果发生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者。不作为共犯只应分为不作为正犯和不作为帮助犯,不作为教唆犯难以成立。不作为帮助犯对结果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不作为正犯必须是条件关系式的“没有此不作为即没有此结果”,而应该是促进了正犯的结果,使其更容易发生。[5]
不作为正犯和不作为帮助犯如何区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上述不作为的帮助犯的概念还不能提供明确的区分标准。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针对不作为犯罪提出了“义务犯罪”的概念,他认为对义务犯罪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了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提出的履行义务的要求。[6]也就是说,在不作为犯罪中,只要行为人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作为义务,并且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就成了不作为的正犯。我国学者张明楷则认为“只要行为人处于保证人的地位而没有履行义务,就符合正犯的要求,而不可能成立帮助犯”的主张是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7]但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正犯的成立也是要以法益侵害的实现或者威胁为必要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有作为义务而没有履行,但也没有发生侵害结果,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不作为正犯的。对此就不能说是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其恰恰是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日本的通说则认为,正犯性是通过对引起构成要件的结果的支配来判断的,那么出于不作为而对故意实现构成要件的直接行为人予以参与的人来说,原则上就不能肯定成立其正犯性,而仅止于成立出于作为形式的正式的共犯而已。[8]但是,这种观点可能导致不作为正犯的成立几乎不可能,因为似乎所有的不作为共犯都至少是不作为帮助犯,在无法确定是不作为正犯还是帮助犯时,就会倾向于成立不作为帮助犯来处罚,这会造成可能应以正犯来处罚的却以帮助犯来进行处罚的不公平。更何况,从本质上来讲,不作为犯正犯的不作为犯罪与作为犯罪中的行为人的犯罪控制来比较,也处于犯罪支配的地位,正如罗克辛所说的:“在控制犯罪与义务犯罪之间区分实行人与参加人时呈现出来的重大区别,当其实行人概念在‘符合行为构成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个最高基点上同时发生时,也没有任何改变。”[9]
具体到本案中,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不作为帮助犯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李某的先前行为负有阻止郑某强奸犯罪的作为义务,他违反这一作为义务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对郑某实施的侵害陈某性的自主决定权具有因果性,并最终导致了郑某侵害陈某性的自决权的法益侵害结果。也就是说,是不作为的李某对犯罪同伙郑某具有犯罪阻止义务,且二人对结果均具有排他性的因果支配,即这时陈某性自决权的法益处于紧迫危险状态,完全依赖于具有作为义务的李某的作为义务的履行或者作为犯的郑某的中止强奸行为才可能不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所以,李某并不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促进了郑某的实行行为,使其强奸行为变得更加容易,而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支配了犯罪过程,应该成立强奸罪的不作为正犯。本案是典型的不作为与作为相结合的共同正犯。这里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情况是,李某在郑某强奸的现场对郑某还起到了心理上的帮助作用,是郑某强奸的作为帮助犯,但笔者认为这里的作为帮助犯可以被不作为正犯所吸收。
而且,笔者并不认为因为李某在强奸中是不作为的实行犯,因而就应该认定为主犯。在我国主犯与实行犯(正犯)、教唆犯,从犯与帮助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行犯(正犯)也可能成立从犯。本案中,如果因为李某是实行犯(正犯)就认定为主犯,一方面恐怕李某本人会不服,他毕竟没有实施奸淫行为;另一方面,国民恐怕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处罚结论,毕竟李某没有实施奸淫行为,却认定为强奸罪的主犯进行处罚是否太过严重了。因此,认定李某在强奸中虽然是不作为的正犯,但是只起到次要作用,认定为从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是妥当的。
[1]李勇:《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本案是2011年笔者作书记员时协助李勇检察官办理的真实案件。
[2]参见李勇:《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笔者原先同意李勇检察官的这种意见,后来又改变了看法。
[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154页。
[4]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99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154页。
[5]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行为的特别表现形式》(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2页。
[7]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395页。
[8][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5页。
[9][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行为的特别表现形式》(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来源:《中国检察官》
作者:吴超令